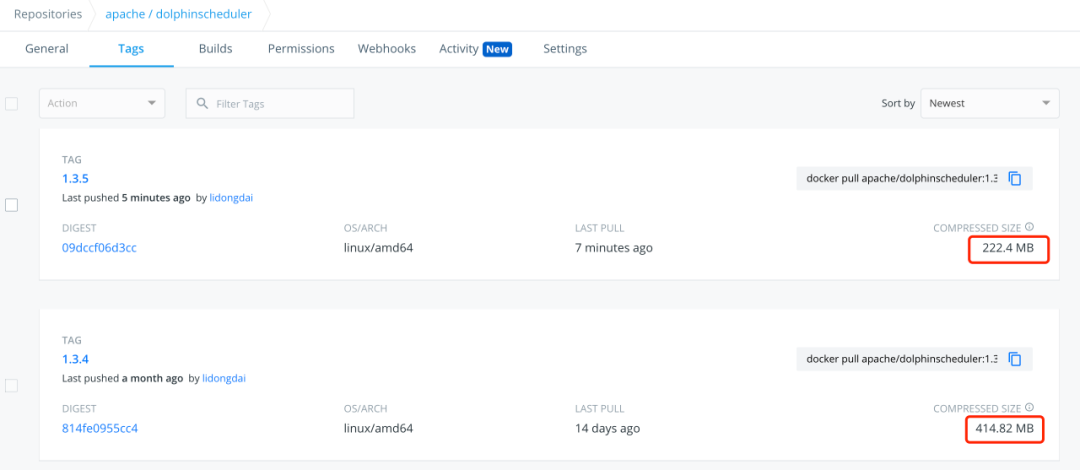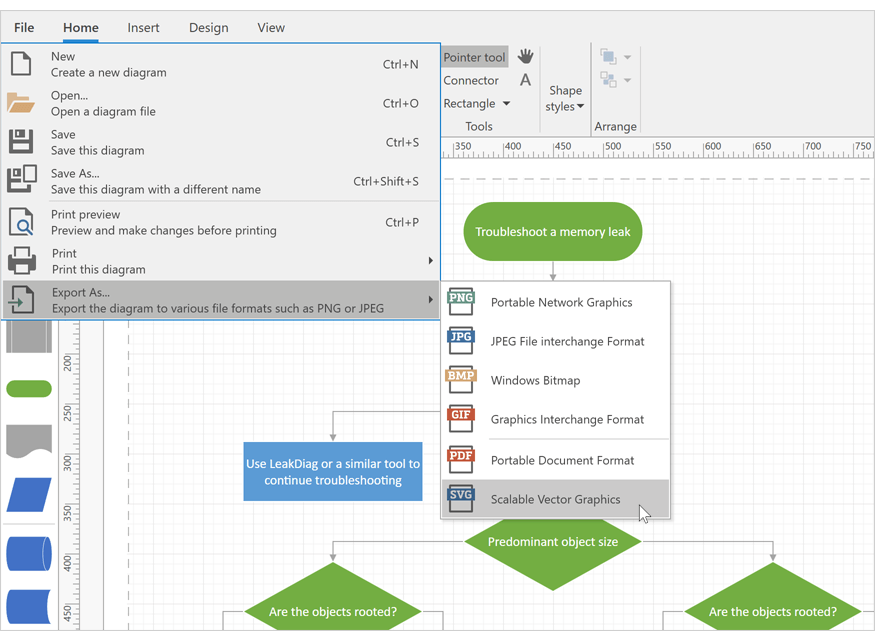随着注册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影响力增大,对被控侵权标识是否与注册商标近似,以及被控侵权商品是否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似的认定标准也相应宽松
2018年12月14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宣判了原告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下称“腾讯公司”)等诉被告深圳市微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微信食品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下称“微信食品案”)。在该案中,原告腾讯公司以其分别核定使用在第9类“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等商品上注册的“微信及图”“Wechat”注册商标,以及核定使用在第38类“信息传送、计算机辅助信息和图像传送”等服务上的“微信及图”“Wechat”注册商标(以下合称“‘微信’商标”)为权利基础,主张被告在“餐厅”“超市”及“网上商城”等服务上使用“微信食品”“WECHAT FOOD”标志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已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专用权。
法院认定“微信”商标构成驰名商标,并认定被告的行为既易造成相关公众误认为被告(及其提供的服务)与原告存在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关系(混淆),又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商标与涉案驰名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从而不正当地利用了原告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并减弱了原告驰名商标的显著性(淡化)。因此,法院认为,被告的前述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驰名商标的专用权。
在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3年修正)(“《商标法》”)下,除驰名商标外,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直接侵权以权利人和侵权人的(1)商标相同或近似,以及(2)商品(含服务,下同)相同或类似为必要条件。只有驰名商标的权利人,才可以享有“跨类”保护,将禁用权的范围扩大到与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既不相同也不类似的商品之上。在“微信食品”案中,原告的微信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及服务与被告使用侵权标志的商品及服务分属《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区分表》”)的不同类别,如不主张其“微信”商标构成驰名商标,则需要突破《区分表》的划类证明商品和服务类似,证明难度很高(虽然根据判决来看未必不能),在此情况下,原告主张“微信”商标构成驰名商标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社交网络平台的霸主,原告列举了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数据,成功地主张了“微信”商标为驰名商标,进而成功地主张了被告的行为不仅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还淡化了其驰名商标。在此过程中,商品的类别差异甚至都不是法院考虑的焦点问题。
“驰名商标”认定犹如天堑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犹如天堑,难以逾越。“微信食品”案中原告却能举重若轻,着实叫人羡煞。至少“非诚勿扰案”的原告金阿欢应该会很羡慕。在“非诚勿扰案”中,原告以其注册在第45类“交友服务、婚姻介绍所”等服务上的“非诚勿扰”商标,诉江苏电视台等在其《非诚勿扰》电视节目使用“非诚勿扰”标志的行为商标侵权。一审认为被告的服务与原告注册商标核定的服务不类似,二审则认定类似,再审再度反转认定不类似。一起两落,“非诚勿扰”商标权人还是绕不过“服务类似”这道门槛。值得注意的是,再审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指出,即使如原告所主张,被诉《非诚勿扰》节目与“交友服务、婚姻介绍”服务类似,但涉案注册商标本身显著性低,亦未经过原告长期、大量的使用而获得后天的显著性。而被诉《非诚勿扰》节目,经过长期热播为公众所熟知。即使被诉节目涉及交友方面的内容,相关公众也能够对该服务来源作出清晰区分,不会产生两者误认和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微信”商标和“非诚勿扰”商标代表了注册商标的两级。从商标本身的角度看,和“微信食品案”“非诚勿扰案”至少反映了三点:(1)注册商标专用权首先产生于“注册”本身,一经行政赋权(商标局核准)就具有一定的排他权利。对任何一个市场经营者来说,如果其商标和服务不巧与他人注册商标及其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似,那么该经营者就可能面对真实的商标侵权风险,无论注册商标权人是否对其注册商标进行了实质性的商业使用。“注册”是商标权的第一次飞跃。(2)商标权的权利根基终究要回到“使用”上,因为只有真实地使用才真正产生并扩大商标的识别功能,而商标侵权的判定也势必要着眼在相关公众的“混淆的可能性”上。注册商标结合真实的商业使用,则如虎添翼,不仅其禁用权范围随其知名度的提高而随之扩大,而且其因注册而获得的专用权基础也将更为稳固。(3)当商标经使用而达到“驰名”的程度,它已经不仅是指示商品来源的工具和承载商誉的载体,它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无形有质的权利,并享有与其驰名程度和显著性相适应的“跨类保护”。
而当一个驰名商标驰名到“微信”的程度,它在相关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和识别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可以不受商品或服务类别的限制而普遍地为任何营业加载商誉(或识别度)。当一个商标成为“微信”,注册与否已经不再重要了。
从商标的发展历程来说,“微信”商标已经到了一个商标能达到的极致,成为一个“完成体”。然而,不是每一个注册商标都叫“微信”。对于绝大多数注册商标的权利人而言,商标的近似(包括相同)和商品的类似(包括相同)是维权之路上必须迈过的“火焰山”。相应地,对于被控侵权人而言,以不侵权进行抗辩往往也着眼于商标的不近似和商品的不类似。缘何注册商标的保护范围要受商标近似和商品类别的限制?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到底是基于 “注册”还是基于 “使用”?为什么驰名商标就可以“跨类”?是否可以彻底抛开《区分表》?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离不开对商标本质和注册商标专用权基础的探析。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基础
首先,对商标识别功能的保护决定了“混淆的可能性”是商标侵权判定的基本标准。
通常认为,商标法保护商标的基本功能,即保护商标的识别性。因此,商标法保护的也并非商标本身,而是商标的有效传递信息的指引功能。从经营者的角度,商标是其商誉的载体,也是其向消费者表明商品来源、质量的重要工具。从消费者的角度,商标(因其识别功能)可以帮助其有效地评估商品的品质,从而降低搜索和交易成本。因此,商标侵权行为侵害的不是商标标志本身,而是商标的识别功能。因此,商标侵权的判断基石是(是否妨碍了商标的正常识别功能而造成相关公众)“混淆的可能性”(likelihood of confusion)。我国《商标法》也在商标侵权判定中引入了“混淆的可能性”的条件,不过《商标法》规定的是“容易导致混淆”,而非“混淆的可能性”,从文义上看,应指需达到较大可能导致混淆的程度。
其次,“注册”本身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权利基础之一。
但是“识别性功能”理论难以完全解释我国法律对于未注册商标的歧视。商标注册人一经商标局核准注册商标,即获得受法律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连续三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并且司法实践中也将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所称的“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概括为不以使用为目的、而规模性抢注他人在先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标并囤积,或者抢注多个不同的在先知名商标的行为。但是商标的注册并不以“使用”(或“具有使用意图”)为前提条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使用权和禁用权的行使更不以注册商标已经实际使用为前提条件。并且,注册商标专用权侵权不以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为要件:侵权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而未注册商标如想得到保护,条件则严苛得多。对于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主要体现在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项。该项禁止经营者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结合这两条,可以看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未注册商业标识(包括未注册商标)的保护,通常以该注册商标具有“一定影响”,且侵权人具有过错为前提。而在注册商标与未注册商标的直接对抗上,除非注册人与在先未注册商标使用人之间具有合同或其他信赖关系,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在其商标具有“一定影响力”之前,通常并不能获得排除他人将该未注册商标进行注册的权利。并且,如果注册商标注册已经超过五年,则在先的未注册商标即使在注册当时即有相当的知名度,但只要未达到“驰名”状态,在这场竞争中也将永久落后了,未注册商标的使用人对其商标的使用将被限制在原使用范围内,而且还要加上适当的区别标识。
从逻辑上说,注册与否并不会实质影响商标的“识别性”。影响商标的“识别性”的根本因素在于商标的使用和因此产生的在相关公众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苏国荣、荣华饼家有限公司等与北京当代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一案中指出的,“商标的价值和作用在于使用商标,商标使用是发挥其标识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体现和提升商标价值的根本途径”。如果对商标权的保护本质上仅在于保护商标的识别性,那么对于注册商标和非注册商标的保护就不应区别对待。所以,合理的解释是,立法者从平衡公平与效率的角度出发,为了方便市场管理、落实责任人,鼓励甚至要求经营者注册并规范使用商标,以敦促经营者保证商品质量,保障市场参与者利益。为此,法律给予“注册商标”注册人超出未注册商标使用人的保护。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广东蒙娜丽莎集团与广东蒙娜丽莎建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蒙娜丽莎案”)中指出,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国家机关依职权授予的,其权利来源于注册登记的效力,系经法定程序确认的独立权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商标注册和不动产登记一样,都是市场统一管理的需要,而注册商标的权利的基础之一也正是“注册”本身。至少,因为注册商标经过统一公示,法律上拟制其具有我国法律领域内的显著性,所有的在后使用者均有退让的义务,而不需要像未注册商标那样,需要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具有排他的力量。
不同保护侧重对判定影响不同
司法实践似乎阶段性地在侧重保护“注册”和侧重保护“识别功能”之间摇摆(或平衡)。当侧重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因为“注册”/国家机关依法授权而产生的专用权利,法院在侵权判定中会更多地强调被控侵权人对注册商标的避让义务,在判定混淆的可能性时,较少地考虑被控侵权人及其被控侵权标志的知名度以及被控侵权人是否有盗取注册商标商誉的意图对侵权认定的影响。在认定混淆时,既考虑正向混淆,也考虑反向混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与周乐伦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新百伦案”)中认定,因为被告的行为导致相关公众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被诉侵权人的商品(或服务),割裂了原告与其注册商标权之间的关系,所以其(侵权)行为导致了“相关公众的混淆”。最高人民法院在“下关沱茶案”中认为,注册商标人“不仅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类似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标识,更有权使用其注册商标标识其商品或者服务,在相关公众中建立该商标标识与其商品来源的联系”。
“如果认为被诉侵权人享有的注册商标更有知名度即可以任意在其商品上使用他人享有注册商标的标识,将实质性损害该注册商标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基本功能,对该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基本性损害。如果被控侵权人的行为导致相关公众将商标权人的商品(或服务)误认为被诉侵权人的商品(或服务)或者误认商标权人与被诉侵权人有某种联系,属于实质性妨碍该注册商标发挥识别作用,构成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而在侧重强调商标“识别性功能”的判例中,注册商标本身的使用情况,以及被控侵权标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侵权认定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非诚勿扰案”的二审判决和再审判决是体现法院不同的侧重会对判决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极佳例子。
从《商标法》的规定看,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产生来源于注册(行政赋权)。侧重“注册”的重要性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也有利于保护市场秩序以及注册商标权人对国家机关行政许可的正当信赖利益。因此,无论注册商标权人是否已经实际开始使用其注册商标,其对注册商标因“注册”而依法产生的专用权受法律保护,其他市场主体也理应合理避让。
但另一方面,商标与(著作权法下的)作品或专利不同,其本身与智力创作没有多大关系,既不要求新颖性或创造性,甚至也不要求自行创作,而是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从公有领域中获取。既然未经使用(并实际发挥一定的商品识别功能)的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实际不过是来自于“注册”本身,而商标注册人选择商标并进行注册的行为本身对于社会的智力成果并无多大增益,则对于未经实际使用而产生一定影响力的注册商标的禁用权范围也应从其注册的标志及核定使用的商品两方面进行严格限定,作者个人认为原则上不应超出其使用权的范围。
法律保护“注册商标”根本上是为了鼓励市场参与者注册其经营标志并进行使用。因此注册商标如果依法注册并依法使用,则其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的专用权利也将更为稳固,而不受后来的(更有影响力)的市场参与者的干涉。“下关沱茶案”中的原告可能代表了《商标法》意图保护的相当大一部分的市场参与者,他们依法注册其商标并依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使用,或许没有很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但对其注册商标,在其核定使用的商品和服务上,足以产生排他的专用权利,不受其他市场主体(哪怕是更有市场影响力的市场主体)的妨碍。
随着注册商标的实际使用范围越广、程度越深,沉淀的商誉越高,市场影响力越大,其禁用权的范围也就越大。从商标侵权判定司法实践来看,主要体现在随着注册商标在相关公众中的影响力增大,对被控侵权标识是否与注册商标近似,以及被控侵权商品是否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类似的认定的标准也相应宽松。当注册商标因使用而“驰名”,则可能享有与其驰名程度相对应的“跨类”保护。(陈绍平)
稿件编审:贾宝元 编辑: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