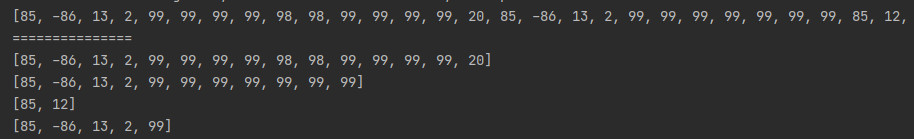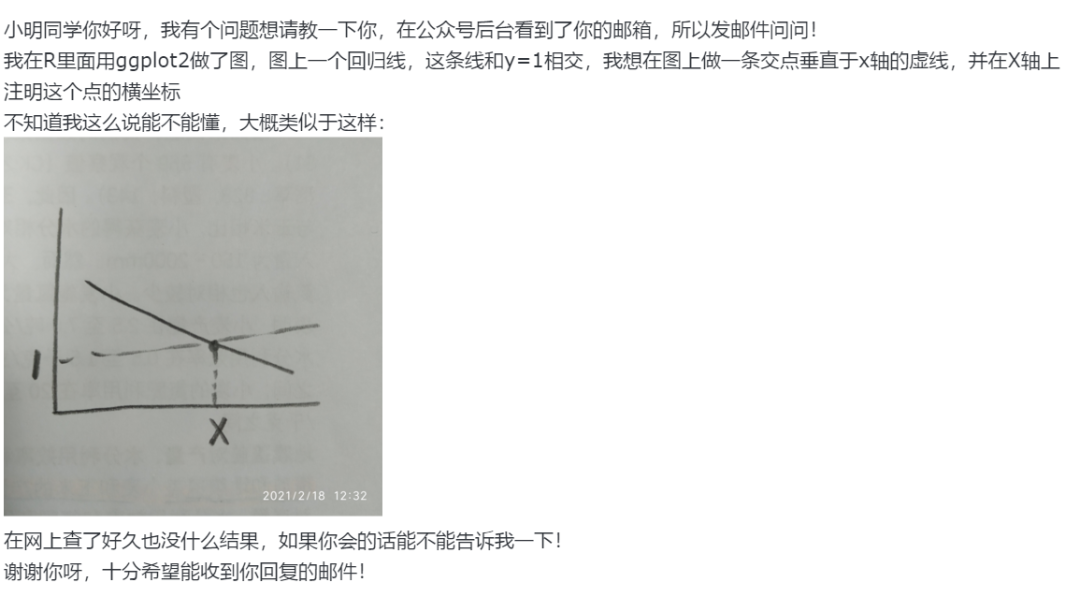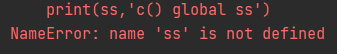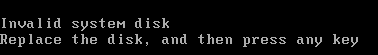邢海洋 1990 年从北京大学地理专业毕业后,先后在一家期货公司做培训师,在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做分析员。1996 年,他辞去分析员的工作,加入改版不久的《三联生活周刊》,撰写财经评论和理财专栏。不久,他碰上“亚洲金融危机兜头而来,接下来是互联网泡沫的泛起与破裂”。
那当口,经济和投资环境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新经济”,是在 1990 年代的美国最时髦的词汇,人们都相信,传统制造业的经济形态将会转变为科技经济形态。振奋人心的证据随处可见,邢海洋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介绍美国订购机票的网站 Priceline 市值超过了几家航空公司的总和。

到了 1998、1999 年,“新经济”的风潮蔓延至中国。在开始盛行的电视股评节目里,分析师们言必称“新经济”,“互联网”。1999 年 5 月 19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称股市潜力巨大。沪指从 1047.83 点上涨至 2245.44 点,涨幅 114.3%。
不过最风光的公司联想是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几家后来重要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邢海洋记得,2000 年前,几乎没有私营公司在 A 股上市。关注证券市场,彼时和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两件事。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投资渠道比现在更少,新的趋势无法成为他们投资的新选择。
这同样体现在邢海洋的专栏文章里,比起鼓吹新机会,更多普及经济学常识。《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的主编朱伟称,邢海洋的文章“构成经济启蒙时代一种先进的方法论”。
1999 年,邢海洋离开《三联生活周刊》,去美国念书。美国人正对经济无比乐观,但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致全球变暖让他们深感焦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邢海洋修读土壤学,研究土壤如何固氮,同时把在美国的见闻寄回中国,以邮件的形式。
2000 年也是加州淘金热 150 周年。邢海洋在这一年撰写了《卖水的赚了大钱》,对比淘金热和互联网热。邢海洋指出,在 100 多年前的淘金热中,赚大钱的是卖铁锹的萨母·布瑞南和淘金工人工作服——粗布牛仔裤的发明者李维。后者是 Levi’s 的创始人。而在 2000 年,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是“互联网设备制造商”思科,首富是 Oracle 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两家公司都在硅谷,却都不是最热门的 ‘.com’ ,一家只生产数据库,另一家则专注于网络硬件设备。”
那时的美国青年与现在的互联网上的创业者有着同样的愿望,一年的辛苦换来一辈子的清闲,但后来的绝大多数离开加州时都是穷困潦倒。事易时移,今天从“.com”出来的年轻人不会再像拓荒者那样窘迫,但很多人的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不免破裂。电子玩具网站曾经是去年圣诞节时最耀眼的礼品网站,公司一上市股价达到七八十美元,没过几个月,跌到了 5 块。类似的网上心理咨询,妇女社区之类的网站均是一落千丈。通常,上市后公司内部人士抛出股票都有一段冻结期,去年和今年被互联网吸引过来的年轻人手里捏的多将是一堆无用的期权。(邢海洋《卖水的赚了大钱》)

这一时期,他的专栏文章还提出了对 Ebay 的看法。Ebay 非常热门,1999 年的营业额为 93 亿美元,但邢海洋认为它依然“很不成熟”。
按经济学家的说法,这样把买卖双方聚在一起的竞价最接近于理想状态的市场经济,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走向。……按理说,聚集了如此多的竞价人,最后的成交价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个合理的水平。但我几次得手的汽车拍卖,却是以卖主给我写私人信件,问能不能多出一两千结束。……岂不说明这个巨大的市场并没有消灭磨擦,反而是没有效率的。(邢海洋《网上拍来的汽车》)
邢海洋是在美国经历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在那之前,他注意到新墨西哥州一大批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都打算转到计算机系,好跑去硅谷找一份工作。但随着纳斯达克指数大幅下跌,媒体开始拿 1930 年代的大萧条和当时的美国类比,人们一下子走到了反面,“只要财务上好看,统统被怀疑是财务操纵。以致全面经济复苏的讯号也挡不住科技股票在华尔街上节节败退”。美国大学生在 2002 年经历了 10 年来求职最艰难的一年。各个行业都是如此。
不过,邢海洋记得,这些一心想转到互联网行业的人都找到了工作,并留了下来。
当然,因为美国经济动荡,当时归国的人也不少,“回国的机票都涨了几百元”。
淘金没那么容易,也许需要另辟蹊径;但淘金热过去,一切也并没有那么糟糕——是邢海洋当时提出的观点。他在一篇专栏里拿互联网行业和英国的铁路投资热潮、运河开凿作比较,认为“电脑通讯互联网全被一股脑儿认为没有了发展空间,连今年软件业恢复两位数的增长也被当成误导”,是投资者对一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过程认识不足。包括英国的铁路发展在内,“历史上,经历了一轮投机后,技术革命会以更稳健的方式发展,直到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2002 年圣诞季,邢海洋报告了美国互联网零售商的漂亮业绩。“连续 8 周的节日期间获得了比前一年多出 15%的增长,网上共售出 138 亿美元的商品。”
没多久,邢海洋回国。网易、搜狐和新浪在纳斯达克的股价此时涨回来了一些。“在新浪网或搜狐的主页,经常出现‘中国概念股大涨’的题目。”网易的发行价是 15.5 美元,此后最低跌至 0.51 美元,但现在回涨至 12 美元。丁磊也因此成为胡润富豪排行榜当年的首富。
包括淘宝网在内,新的互联网玩家出现了。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对财富有了更多心得,他们对新的投资机会更敏感。邢海洋回到《三联生活周刊》继续撰写专栏,涉及的范围变得更广:艺术品市场、房市、股市、黄金。
因为喜欢上画画,邢海洋搬去了北京宋庄镇的小堡村。他买下艺术家马越的房子,发现镇政府成立里艺术促进会和“文化造镇”办公室,因为油画价格在一年里飞涨,宋庄一下子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房价差不多翻了一倍。在《油画的郁金香之旅》里,邢海洋写道:“油画市场本来有一个极端小众并且稳定的投资群,也正因此,这里没有赝品,没有无尽的口水。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油画能赚钱了,这个市场变成大众,喧哗起来。”

和互联网行业一样。
在 2009 年出版的个人文集《投资物语》后记里,邢海洋表达了他对中国市场的困惑:“经历了如此多的市场动荡,是否说明了我们这个市场仍处于蛮荒时代。”开启经济启蒙时代似乎比想象中更困难。2007 年 5 月,A 股市场大幅上涨,当时的报道称一天内有二三十万的开户数。
可惜的是十几年间,中国互联网领域涌现出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都奔赴海外上市。因为有严格的收益门槛,那些在 A 股上市的企业都被海外率先融到资本的企业甩在身后,陷入胜者获取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陷阱里。…………因为没有好股票,着眼于未来的长线投资者远离了 A 股。又因为缺乏稳定的投资者,好股票也不愿驻足,这是一个生态退化的典型环境,世界范围内,恶性循环的例子不胜枚举。(邢海洋《被出口的好股票》)
我们在北京常营的一家咖啡馆和邢海洋进行了采访。采访快结束时,邻座的一位先生突然加入了我们的对话。他于 1990 年代中后期在卡耐基梅隆读理论计算机,补充了一些 1999 年前后的有趣背景。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创业当时并不是一件人人追逐的事。当这位先生宣布要编写网页时,他的同学显示出不屑:“这是 F2 才做的事”。F2 指陪读签证,持 F2 签证的人“通常只能做些和计算机擦边的工作”。
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邢海洋和他的观点,以下是他的口述:
1996 年之前,我还在证券咨询公司做分析员,每天写收盘的股评,再通过传真发到给证券公司,他们会贴在公示栏里,通常在一楼大厅,给他们的客户看。
当时尚未有“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讨论,有意思的地方是,电脑出现了。在交替的时期,一种新东西出现了,大家就开始追这东西。
最开始的时候,股民看行情全是在证券交易大厅,写字楼一层最热闹的地方,外边围着特多人,价格板像电影屏幕似的,不停地翻。中国人特别爱看走势图,那时候每个证券公司就在散户大厅里配两三台电脑,就成了一些老油子、老股民的专利。他们就围在那儿,不停地翻呀不停地看,给别人吹牛什么的,显得很神秘。
在证券咨询公司做分析员,一人一台 286 或者 386 电脑。老得盯着它,我本身对价格挺敏感,弄得人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沮丧,后来我就转行了。
在《三联生活周刊》,有个阅报栏,订了好多报纸,一位现在已经退休的吴老太太每天就把好多报纸钉在那儿,我们都看。突然就有一天,他们说有个新的获取的信息的方式了,新华社开放了内网,特别简单的字体,但你挑一个东西他就能搜出来。
三联那时候刚成立,号称是“豪华配置”,几乎一个人都能配一台电脑。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笔写的,查东西基本上就是到单位上网搜索,搜完了还要打出来。因为家里即使有电脑也没联网。
现在人们投资渠道少,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渠道,跟海外市场也是隔绝的,所以出现了很多特奇葩的事。北京当时推出了一个商品交易所,炒绿豆。最后价格就单边上涨,逼得空头从山西开着卡车、拉着小豆往北京跑,来交货。如果是一个成熟市场,和国外能联通,大家能套利了,就不会出现这个事儿。
那时候大家也没有理财的知识和理财观念。我讲过一个“复利”的故事——在一个棋盘上,第一格放 1 粒米,第二格放 2 粒米,第三格放 4 粒米,之后每一小格都比前一小格加一倍。最后国王发现把粮库都放空也不够,因为要把 64 格棋盘放满,需要 184 亿亿粒米 ——(主编)朱伟就很高兴,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概念。有时候就像“二传手”,在北京图书馆有一个提供港台刊物的书籍阅览室,港台普及理财的小科普书语言简短,讲的故事也怂人听闻。你把故事再重述给国内的读者就足够了。

关于三大门户在纳斯达克上市,我想我应该也关注了,但现在就忘了。现在回过头想,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事在人为,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对来说是挺宽松的。我是 1990 年大学毕业,那时候特烦人,就比如你要出国,必须先签一份合同,因为国家培养你了,你必须有五年的服务期,然后才能拿到护照。可是到了 1996、1997 年的时候,虽然不像现在这样恨不得到派出所就能拿到护照,但是只要去一申请也就可以了。外汇市场也是,你到处都能看见有人在银行门口换美元,没有那么多限制。
那时候在国内上市的都还是传统公司。顶多是卖电脑的公司,吹牛自己要转型。2000 年左右国内股市起来一波行情,是受美国股市的影响。我写过一篇文章,讲订机票的网站 priceline 的市值超过了好几家航空公司的总和。美国股市的泡沫大,这边却够不着,完全没办法去(投资),国内的创业公司也是在国外上市的,所以国内股市就弄些“伪泡沫”,制造一些概念。资本市场这一块,国内一直管得那么紧。2000 年之前,我的印象中几乎是没有民营企业上市的。
当时国内的证券市场也跟互联网行业离得挺远的。国内市场特别不透明,普通投资者根本接触不到创业,创业本身又是非常危险的行当。
我不是一直在弄股票这些事嘛,正好碰着朋友介绍我认识一哥俩,他们一直想创业,我就说,干脆咱们编一个证券软件。的确那时候看行情是特别费劲的一件事儿。如果把这个软件编出来免费发给大家,咱们不就等于获得了一个进入互联网的入口了?从这个入口可以延伸出别的范围,像一个门户似的。
这哥俩呢,哥哥特别聪明,他是学英文的,很有鼓动力,每个人见到他,几句话就能被他给说得跟着他一块儿亢奋。当时他包了《中国企业家》的版面,宣传“新经济”和互联网。弟弟能写代码,还不是程序员出身的,是自学的。他们之前做旅游软件赚了一小笔钱。我们三个就一块儿。那时候我三十一二岁。
我们弄了个小公司,在老单位的楼里边弄了一个办公室,挺大的,差不多有 50 平,就我们仨。买了 17 寸的显示器,特高兴,因为那时候 17 寸的显示器真是太了不得了,几乎没怎么见过。
我爱人那时候正好出国了,我就跟他们哥俩生活在一起,住在印刷厂的大仓库,边上就是员工宿舍和推销药材、卖医疗器械的公司,每天吃大锅饭。他们是贵州人,弄一个小火锅,买各种青菜什么的。有点像一些共产主义年轻人。就这样过了差不多半年,哥哥变得越来越狂躁,到最后每天停不住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后来他得了甲亢,就只能停止。好像他跟我说过一次,还真有公司准备给我们投钱了,投 50 万。他英文特别好,有去找那些国外的投资公司。但我们那时候已经晚了,错过了第一波 IDG 乱投。
你都不知道现在成功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你没成功过,你就不知道你跟他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999 年,我去了美国。当时我还把(我们做的东西)做成了一个光盘,我说我拿去美国那边,问问这个东西有没有前景。
其实我在美国的学校是在新墨西哥州。虽然在沙漠里那么一个小城市,但也能感受到周边的氛围。经常发生些什么事儿,我就写,写完了传回来,就在《三联生活周刊》保留了一个专栏。
我有一个同事叫刘怀昭,当时在美国,她的爱人叫张猛。我去那个加州找他们聊天时,张猛可能就在加州做一编辑。可那时候真是人才供不应求,当时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 IDG 居然让他回北京来当 IDG 的总代表。
国外当时流行炒域名,有人就靠这个发财。我自己还买了几个域名,其中一个叫 ehumanbeing,电子人类。但第二年就发现没人理我,还得接着交维护费。那时候你要是抢注域名,越短越好,肯定要搜一下,一看所有键盘上的字母都没了,然后几个字母的组合,发现又都没了,然后单词组合。国内好像喜欢抢数字域名,数字域名特别火。

当时 AOL 就是美国在线挺热闹的,后来大家一看,人家就是一个自己公司的名字,也成了行业巨舰。不像咱们这儿弄得那么邪乎,弄得那么神秘,你得做出来。当时有家公司 buy.com,域名价值感觉比 ebay 还好,但是最后他们就没做出来。
好多留学生拼命地看广告赚钱。那时候中国是买不到便宜的东西的,什么东西都挺贵的,也根本没有促销手段。到了美国,大家在报纸上剪一个 groupon 就觉得挺高兴。后来发现居然看电脑能赚钱,download 一个小的插件,不停地给你推广告。你看了广告,他们就会一个月给你寄二十三十美元。有的留学生还在论坛里给自己起名“烧瓶”,其实就是买东西 shopping 的意思,大家开始有意地在网上攒各种各样的优惠券。即使你不攒,在网站上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用户,没准这个网站就会送你一个显卡,那个网站会送你主板。有人居然说,我要这样攒出一台电脑,尽管电脑也没多少钱,但就是弄这东西觉得挺上瘾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烧瓶”帮的风光与悲哀》。
但那个时候最明显的感觉是,不管你学什么,因为找工作是唯一的指向,恨不得连学文科的人也想办法选修计算机的课。你的老师肯定不愿意,所以你必须做好打算,计算机那边的老师什么时候允许你转系,先去选课,表现优异,然后再转系。转完系,拿着这个去硅谷工作。
我们学校离墨西哥近,墨西哥人乐天,很多人能在这里上学是政府资助的,所以好像没这样。但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做的很多,尤其印度人更是这样。
我在美国学的是土壤,我也去学了一门计算机课。但我没想去硅谷工作。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四五岁了,没精力像那个年轻人似的那么折腾,也挺想回来的。只是因为之前我在北京和那俩小伙子一块儿做证券软件,用的是 Java 编程,我就去学 Java 了。Java 当时特别流行。学起来,我就发现这东西也是挺难的。后来分组做项目,我还是找了一个数学系的人,他给帮助做出来的。一个小的电梯模型。
那些转到计算机系、想去硅谷工作的中国人基本都成功了。不去硅谷,也去别的地方。所以挺有意思的,泡沫破裂,股指从 5000 多点最后跌到 1000 多点,居然他们也都找到工作了。而且还面临这么一个困难,大家拿的是 H1 签证,如果要被辞了,十天之内,必须得换到另外一个工作,要是换不到就没有合法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待了下来。
从媒体上看萧条得简直不行了,天天都像是天要塌下来的感觉——这个公司崩盘,那个公司裁员,发不出工资,全是这种。但泡沫可能只是发生在特别虚的地方,真正搞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应该都没问题。
后来我还就此写了一篇专栏。当时国内股市也在跌,大家心情都不好,我就给大家讲,当年我去硅谷的时候没开车,只能去坐“灰狗”长途巴士。灰狗站都是特别残破的市中心,原先大家都恨不得拿一张 AAA (美国汽车协会)送的免费大地图,我去的时候没有那种地图,但我可以去市立的图书馆,在网上搜到地图,找到灰狗站在哪儿,然后再走过去。所以我就说,你能感觉到互联网是有用的,它并不是没用,只要是有用的东西,就慢慢能够生根发芽。

我在 2002 年回国。那之前我去普渡大学读 MBA,但十天之后就退学了。一天要看一百张 paper,我睡不着觉,挺焦虑的。一看那些年轻人,好像都特别精神饱满。
一回来,我就记得大家开始关注新浪了,说新浪怎么从五块钱变十块钱,那半年里一下又涨到五六十块钱。
国内新的公司是淘宝。三联有一个同事,我知道他在 2003 年还是 2004 年开了一家淘宝店,卖窗帘。他让我买他的窗帘,当个托儿,我就买了。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同事什么的都开始干这事了,挺有意思的。我都是最近一两年才开的淘宝账户。
离开美国时,我还挺信心满满,好歹我在国外修了点金融课,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基金公司。但是变化太快了。我一个学会计的朋友,出国前在学校里当老师,再后来去亚信做兼职。 亚信当时是中关村最棒的网络公司。是美国回来的田溯宁办的。那天她说我们来了一个 CEO,仅仅就是因为那人在加拿大读了一个 MBA,也没听说过他干过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海归”变“海待”,就这么一两年的事儿,回来的人突然就多了。 后来眼看着百度什么的就都起来了。
现在看,我挺对不起看我专栏的人。好多机会也没说。最近我回忆过去的这些事,梳理过去的这些东西,一看百度什么时候上市的,最后涨了几十倍,我才意识到过去挺疏离的。那时候关注更多的都是生活表面的,比如说石油涨价,大宗商品,粮食。
邢海洋:
前证券咨询公司分析员。1996 年 8 月加入《三联生活周刊》,撰写财经评论。2009 年,个人文集《投资物语》出版。1999 年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时,经历了美国的互联网泡沫及其破裂。
题图来自 Markus Spiskeon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