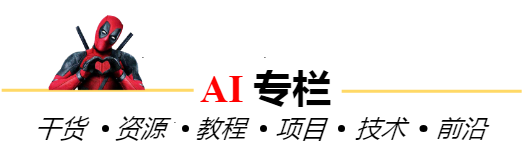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8期,原文标题《器官移植与“孤儿药”:互联网助力》
2016年1月23日,浙江省杭州市阿里巴巴滨江园区内,阿里巴巴员工向农村孤儿送上新年祝福
一天完成一年的量
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终极命题。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想清楚自己离去后肉身上的器官何去何从。
2016年12月22日,支付宝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合作,在支付宝平台上上线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功能。绑定了身份证的实名用户,只需在支付宝搜索框输入“医疗服务”,进入医疗服务平台主页,点击“器官捐赠登记”应用,使用“一键登记”功能,即可注册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整个过程仅需10秒,自愿,亦可随时取消。
平台上线当天,就完成过往一年的登记量;上线两天后,通过支付宝完成器官捐赠志愿登记的数量达8万余人,超过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过去两年半以来登记数量的总和。此前,中国红十字会、“施予受”两大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都于2014年开通了在线登记,但进展一直缓慢,直到2016年仅共有约8万余人。
登记陷入瓶颈,并非由于大众热情不高,而在于此前步骤过于繁琐。过往的器官捐献登记,无论是纸质还是网络登记,都需要填写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超过20余条信息,这让很多有意向登记的志愿者望而却步。
平台上线前的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不愿登记的人中,56%的人选择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我们做过测算,每增加一条,流失率可能会增大20%~30%。”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系统主任赵洪涛说。
支付宝尽可能地简化了登记流程,但赵洪涛还表示,支付宝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上优势不仅体现为便捷性,也集中体现为实名用户规模——当2016年双方探讨合作可能性时,支付宝已是有超过4.5亿用户的金融平台,并且全部进行了实名身份认证,这在中国独一无二。
截至2018年3月11日,该基金会旗下的“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已成功登记28.2461万人,赵洪涛估计通过支付宝渠道进行登记的占到了20万以上。“峰值期每分钟有超过100人登记。”赵洪涛说,这对整个器官捐赠志愿登记意义重大。“‘80后’‘90后’本来对这个事情就不是很排斥,只是需要一个便捷的渠道。”
支付宝的器官捐献一键登记仅是2016年众多“互联网+公益”项目中的一个典例。2016年被不少公益人士认为是“互联网+公益”元年。当年颁布的《互联网慈善发展报告·上海的实践》指出,中国已切换到“人人公益”时代,互联网的兴起为募捐活动和民间自发慈善行为提供了超大规模的全国汇集通路,可以覆盖巨大的用户群体,而且有着很强的用户黏性。
这背后与年轻一代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相关。蚂蚁金服社会责任部负责人李姗说,从支付宝数据来看,“90后”甚至“95后”已经成为公益主力军。对年轻一代来说,公益不再是“做好事”,而是一种日常表达。年轻人参与公益的愿望非常强烈,公益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比起捐款,他们更愿意身体力行地投入公益,感受成就感。”
而不同于传统互联网募捐,阿里巴巴利用自身平台优势在“互联网+公益”上再辟蹊径。李姗说,如果说传统网络募捐属于“互联网+公益”的1.0模式的话,那么阿里及蚂蚁金服则希望借助其淘宝、支付宝等平台优势,嵌入公益项目,打造“互联网+公益2.0”玩法。
不过事实上,“一键登记”项目的上线与推广并非一帆风顺。蚂蚁金服的法律和风控部门的员工曾担心,用户可能出于担心自己隐私被泄露的原因,对该项目提出质疑,况且医疗健康领域在中国本来也是一个负面新闻频繁的领域,遑论器官移植捐献未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2016年7月,就在支付宝内部仍不放心时,苹果iOS10系统针对美国用户增加了器官捐献功能,只需几秒钟便可登记完成。此后,经由美国政府倡议,Facebook等巨头也在开发工具来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发展。这个消息直到项目上线后双方才知道,进而增大了对项目的信心。
“如果早知道美国这些互联网巨头也在推,我们的信心可能会更足。”蚂蚁金服医疗健康事业负责人张梁松说,其他部门同事担心的负面效果暂时没有发生,“可能跟我们的用户以‘80后’‘90后’为主有关,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更加开放一点”。
探路“孤儿药”
2015年8月,杭州萧山区一位出生不到8个月的婴儿患上了婴儿痉挛症,却被医院告知疗效最好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缺药,只能依靠病人自己想办法。
婴儿父亲广发朋友圈求助,但杭州、北京、广州等地都无此药可售。原本是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黑市上被炒到了4000元,还不一定能保证是真药。父亲的求助信息被阿里健康一位曾从事药品流通的员工看到,他联系了能接触到的药品生产厂家和流通商,在求助信发出24小时内,将两盒ACTH通过冷链的方式送到了患者父母手中。
“之前没有特别留意,但那年我们感觉这种需求蛮多的,微博、朋友圈都有。”阿里健康“全球找药联盟”项目负责人梁素娟说,团队此后产生了做一款找药产品的想法,利用互联网手段连接各大医院、药房,乃至药品生产和流通商,而不是靠人工的方式去发帖求助问询。
次年,阿里健康携手国药健康共同搭建“阿里寻药”公益平台上线,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患者及其家属可通过此渠道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紧缺药品,平台会查询药物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时信息。2017年7月,这一公益平台扩大为全球找药联盟。
2018年2月28日,这一天为世界罕见病日,阿里健康首次披露了该平台寻药数据。据统计,截至2018年1月底,在找药平台人工寻药需求中,对罕见病类的寻药需求达6.0%,而中国罕见病病人占总人口的1.2%。超过165万人次通过该平台找药,77.20%找到所需药品。搜索找药排名前32的药品中,约30%为罕见病、重症疾病、感染性疾病的寻药需求。
在中国,罕见病患者寻药难,早已不是新闻。中国有超过1600万的罕见病患者。罕见病,顾名思义,病理罕见,药品亦罕见,许多药物需从海外代购。药品的极度稀缺,让罕见病用药一直有着“孤儿药”的别称。中国孤儿药创新联盟创始人、南京工业大学药学教授郑维义告诉本刊记者,全球大约有600多种“孤儿药”,其中在中国批准上市的仅有140多种,而原材料短缺等复杂的市场原因随时可能导致这140多种药物区域性短缺。
“很多疾病药品很少,在常规渠道上更难找,需要互联网等特殊渠道解决。”罕见病发展中心主任黄如方说。据梁素娟介绍,目前平台对接了超过1万家医院、药品门店的药品流通信息。某些特殊、难找的药品通过直接搜索暂时不能找到,他们便开通了人工客服留言功能,通过建立与各大药品供应商的联系,把用户的需求与药品供应方联系起来,目前约有52%左右的人工找药需求得到满足。
“在中国上千万的罕见病患者中,能得到有效的、稳定的用药治疗的患者估计不足10%。”郑维义说,“所以阿里搭建这样一个平台,有其意义所在,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目前,全球找药联盟的后台已对接了国药系统、拥有3000多家门店的国大药房体系以及300多家有资质的线上药房体系,总共有超过上万家线下实体药店与几百家线上药店,共囊括了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在内的几十万种药物,平台日均流量稳定在1万人次左右。
但在梁素娟看来,这些数据的丰富度仍然远远不够。“美国前三位药品流动批发商占到了整个市场份额的70%~80%,容易统计和打通,但中国较分散,各家数据不一样,并且药品管理是分区而制,数据本身很割裂。”
公益洗牌
张梁松及其团队每年有做一个公益项目的小目标。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上线一年后,支付宝又开始了推行无偿献血领域的尝试。
2016年,支付宝一位员工的父亲做手术,需要大量用血,遂在阿里内网求助,召集大家去做无偿互助献血。献血车来了之后,很多同事现场想去献,但因没带身份证被拒,那时候很多人才知道,原来献血也是需要带身份证的。“在生活中遇到了很多事情,就会直接去用互联网的思维考量。”张梁松说,阿里内部每年会要求员工从事3小时公益活动,这不在绩效考核内。
张梁松找到了浙江省血液中心,提出了一个简化身份识别的解决方案:给每辆献血车上装上摄像头,利用人脸识别进行身份鉴别,不需要身份证。对方一开始拒绝,说献血章程需要一条条改很难,但后面也逐渐意识到了互联网技术对效率的提升。最终,2018年1月,浙江省血液中心与支付宝合作,发布了浙江省电子献血卡,通过此卡刷脸识别,并可实时一键查询全省范围内的献血记录、血液去向、可用血额度等等。
在阿里,公益被当作阿里文化的一种。2015年9月10日,马云通过阿里全员邮件发出“每人每年公益3小时”的倡导,后从阿里数万名员工扩展至450多万名用户。从集团投入上,公益也占据了一定比例。阿里巴巴社会责任部负责人吴耀华对本刊记者介绍,从2010年起,阿里决定每年0.3%的营业额作为公益基金推动公众参与。按照2016、2017财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计算,阿里近两年每年的公益基金都在3亿元以上。
吴耀华介绍,目前阿里的公益事业主要分为三大维度:员工个人受鼓励的公益行为、与阿里业务紧密结合的公益项目、集团战略布局的公益事业等。不同于其他互联网公司在优势产品上做公益平台,阿里选择做平台公益,希望利用自身淘宝、支付宝两大平台优势,将商业逻辑融入到公益价值。其中,首先就是在内部鼓励将公益与各条业务线相结合,以保证可持续造血能力。2017财年,阿里集团上线公益项目23个,包括支付宝器官捐献一键登记与全球找药联盟。
希望工程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认为,阿里的平台公益模式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将公益融入其商业模式中,相比之下,腾讯、京东等则是在产品中加上公益板块,例如腾讯的“99公益日”则侧重在短期内造出影响力呼吁社会募捐、参与,二者策略不同。
徐永光近两年一直倡导中国公益“市场化”和“规模化”,用市场化中的结果导向和规模效益去做公益,以提高效率。他观察到,这些年中国公益圈出现的行业洗牌,出现了“阿里系”、“爱佑系”、“阿拉善SEE系”、“壹基金系”等等,他个人看好乃至支持这种行业力量的有效整合与“洗牌”。
“中国公益需要规模化扩张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供求不平衡。但公益机构推动洗牌的能力还是很弱,所以现在BAT等大型互联网商业主体的进入,成为了洗牌的催化剂,资源会逐渐导向有效机构。”徐永光说,商业机构各自的公益模式不尽相同,但是都在推动公益效率的提升。“他们的动作力度特别大,公益组织自身变革的力度,还没有BAT和京东等外力推动的大。”
瓶颈与未来
虽然项目上线之后效果立竿见影,但目前总共28万的志愿登记量,在赵洪涛看来,还“远远不够”。“按照我们预期的设想,每年得上百万人登记才能补上30万的移植缺口,总体上没有达到预期,但也有一定的影响”赵洪涛说。
他将这归因于后续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项目上线前后几日,基金会联合支付宝通过线上媒体、线下地推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宣传活动,社会关注度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但此后归于平静,当前日均志愿登记量稳定在200~300人范围。
有鉴于此,基金会已打算成立专项基金,对平台的宣传策略设计和具体项目落地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在和支付宝探讨下一步的合作形式。“但支付宝的公益业务太多了,无法分散精力,所以想要他们把这个入口在支付宝中放在前面点。”赵洪涛说。
并且,从志愿登记到捐献最终落地,还有十分漫长的路程要走。志愿登记更多的只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其系统目前还未与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打通,也就是说暂时没有通过支付宝志愿登记成功捐献器官的案例。
赵洪涛解释,在器官捐献整个流程中,志愿登记和临床操作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临床操作可包括,家人同意捐献、医生评估、摘除器官、COTRS系统分配等。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打通志愿登记和临床捐献之间的链接,建立潜在捐献者数据库,主要记录已出现临床症状的志愿者。赵洪涛说:“打通了这个,器官捐献协调员去做家属工作的时候,就能告知他们亲人在生前表达了捐献意愿,如果没有这个支持去跟家属谈捐献,会很困难。”
在赵洪涛看来,后续流程已过于专业,互联网发挥不了太大作用,更多只是起到一个宣传作用,唤醒大众意识。而梁素娟介绍,全球寻药联盟团队成员都有药学专业背景,但日常工作本身就已经很繁忙了,这个平台的纯公益定位,使得团队要花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常常觉得分身乏术。为此,梁素娟一度有考虑找一家NGO全职承接运营。“我们本来是做药品商业的,精力不够。他们更加专业,但技术又是他们的短板。”
而全球找药联盟,也暂时无法满足大规模的代购需求。梁素娟表示,因为政策壁垒的存在,平台暂时打通大规模代购需求,下一步工作重心放将在罕见病、特殊肿瘤的短缺药供应上,用患者需求去联动零售商、批发商和厂家,恢复某些药品的生产和供应,“不排除从阿里公益基金拿出一定费用放在短缺药上”。
同时,不止一位专业的罕见病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罕见病等患者群体通过该寻药平台找药的人依然是少数。黄如方说,目前罕见病患者群体主要的寻药渠道是海外代购。“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患者就是依靠小额代购。甚至病人与病人之间相互借药,这次借了下次就还你一点,代购频率非常高。”
从数据上看,罕见病、特殊肿瘤等疑难杂症通过全球找药联盟获得药的成功率也相对较低。梁素娟透露,罕见病、特殊肿瘤等群体的找药需求满足率比52%略低一点,约在50%上下。出于政策和法律的原因,用户最大的海外代购需求暂时无法在平台上得到满足。
此外,国内的罕见病还有着诊断难的问题。黄如方认为,互联网能在远程会诊、辅助诊断乃至进行慢性病管理上发挥很大作用。“能诊断罕见病的医生非常少,不到500个,并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罕见病患者有上千万之多,还分布在全国各地。” 梁素娟说,这方面他们也在和一些国内知名医疗机构洽谈合作,希望在1~2个细分疾病领域上推动形成一个诊治闭环。